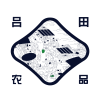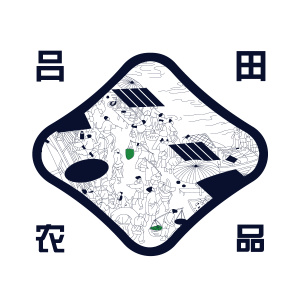每年一月,一大堆电子邮件袭击我的收件箱,提供饮食和七天的果汁清洁,承诺“新年,新我”。消息很明显:目前的“我”很糟糕。但是,如果我减掉10磅,我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我” - 虽然头晕,烦躁,没有乐趣。我拒绝参与。
这并不总是这样。
“你有饮食失调症,”一位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读完11年级后对我说。我们一起坐在格鲁吉亚海岛的沙滩上,当我们啜着冰冷的帕布斯特蓝丝带时,我们脚间的黑沙覆盖着。
“我很好!” 我否认。我没有。
我在南方的亚特兰大市郊长大,那里过分注重外表是常态。那是80年代初,早在有机的慢食运动之前。我的妈妈在奇妙的面包上提供了波洛尼亚三明治,配以橙色电力多力多滋(Doritos),一款奥利奥(Oreo)追逐者以及永久燃烧的头发。一个深情的南方女人叫我“成龙豆”,用亲吻掩护我和我的兄弟,她什么也没有想到。食物是食物。
在她43岁生日的一周后,她在睡眠中突然死于脑动脉瘤。我9岁。
多年来,我们从死亡中re,而过,变成了一个破碎的转盘 - 狂野地旋转着的乙烯树脂,针刺入记录的凹槽,音乐扭曲和war。。食物成了我能控制的东西,创造出一贯的和安全的速度 - 在我生命中的配乐中稳定的跳动。但歌词是苛刻和军国主义的,“没有缺陷允许”。
在高中和大学里,我用Stephen Curry的篮球运球例程的战术焦点和技巧来减肥。在90年代的节食方面,我变得非常熟练:无脂肪食物,健怡可乐,以及日常踏步健美操。完美的学生,完美的身体。完美,完美,完美。
但是,我只能预测到目前为止我完美的幻想。我把每一滴努力都投入到我的学业和实际形式中,但是让其他一切都落空了。成堆的衣服凌乱在我的卧室地板上,我的海军本田雅阁用丢弃的健怡可乐罐和空冷冻酸奶酪杯子膨胀起来。就像一个女人在Instagram上张贴她可爱的孩子的完美照片,而家庭的狗在她身后的肮脏的厨房地板上排便。
20多岁的时候,我搬到了旧金山,开始练习瑜伽。当我的身体静止时,我的思绪放慢了。我终于开始听到我脑海中的声音。我惊骇的说:“你为什么这么胖?” 这是不正确的。但是,我这个有毒的,内心的批评者欺骗了我,把它当作事实。那声音粗鲁而大声,我听了。
随着我二十多岁的进步,我开始相信 - 甚至 - 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不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一种能够让我在今生做出伟大的事情的工具:照顾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爱的朋友,姐妹,女儿和妻子。最后,我的身体会衰退,最终会死亡并溶入地下。但内在的东西 - 我是谁的真正本质 - 永远不会改变。
现在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一年级的儿子和一个二年级的女儿。最近,总部位于伯克利的非营利机构The Body Positive参观了马林县的学校,教导人们克服身体冲突。我注册了一个“在形象迷恋的世界”的研讨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身体形象对于7岁和8岁的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了解到,12岁以下儿童患有饮食失调的住院率正在上升。
事实上,每个人口中的身体不满和饮食问题正在增加,这不仅仅是一个十几岁的中上阶层,甚至只是一个女性问题。更糟的是,25年前几乎不存在的饮食行业现在已经有超过400亿美元的资金。后果是可怕的:神经性厌食症的精神疾病的死亡率最高。
我们生活在一种饮食文化中:饮食里面有什么,什么不在里面,从哪里来的。孩子们看到他们周围的成年人切除碳水化合物或吸入甘蓝汁,酊剂和茶来减肥。信息混乱:爱你的身体,但看你吃什么!吃有机的。没有GMO的。没有面筋。不要太多的盐或糖。但是要爱你的身体就是这样!
孩子们正在学习,如果穿上紧身牛仔裤或者比较小的比基尼,那么自我剥夺是可以的。相反,我们应该教导他们的身体形状和尺寸来自我们的祖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在学校要求健康的身体形象课程,并坚决质疑瘦身是健康的观念。
我的两个孩子是一面镜子,可以保持我的完美主义倾向。当我看到我的反映在他们的眼睛,我知道我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记得让我的内心批评者沉默,“闭嘴!我不听!” 就像我希望他们阻止他们的。
“你有什么信息,你的身体?放学后我有一天问我女儿。她坐在我的车后面,一起sma着粉红色的匡威运动鞋,尘土飞扬。“你必须瘦!” 她说。“你应该减掉10磅。” 她8岁。
就像我教他们系鞋带骑自行车一样,我必须让我的孩子知道如何欣赏人体:一个非常聪明的工具。一个灵魂的容器,决不能说明他们是谁,就像我们完美的形象投射文化是错误地交流的。
今晚,当我们读到他们每晚的故事时,我蜷缩着与我的女儿玛丽娜和我的儿子泰勒。在睡觉之前,我告诉他们重要的是承认那天给你的东西。
“谢谢你这个机构,”我说。“我保证好好照顾它。” 也许我是在向神或宇宙或者我们心爱的大多数聋人的老年英语二传手说话。
“妈妈,停下来!” 玛丽娜哭了。“你真烦人!” 当她不高兴的时候,她的鼻子会皱起来。
我揉了揉鼻子上的线条,大笑起来。我想她是对的。我听起来像一个讲话PBS后特殊。
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个声音。她一直坚持下去。